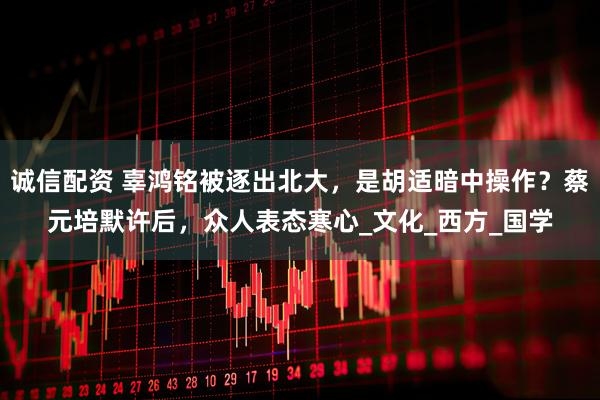
在风云荟萃的民国时期,辜鸿铭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的怪人,当然,他最醒目的怪异特征就是头上的那根辫子。
在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在新旧文化的激烈碰撞里,这根辫子始终都没有剪去分毫,一直孤傲地立在身后,这都是来源于辫子主人的底气。
作为东方国学的扛旗之人,辜鸿铭不仅在中华传统文化上造诣颇深,而且还非常精通西洋科学和语言,是真正做到了中西贯通的第一人。因此,识人善用的蔡元培在执掌北大时才会顶住反封建热潮的压力继续聘任他为北大教授。
当时,新旧文化之争已经到达了白热化阶段,但正是因为有争议,文化也才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生机。
六十一岁的辜鸿铭尽管在年纪上已经步入老龄,但是他仍旧斗志昂扬,誓死捍卫孔教国学的正统地位,与留洋归来的胡适针锋相对。只是他终究因为“保皇”的致命把柄被人揪住,只能黯然退出了北大的文化舞台。
展开剩余91%这是新文化运动一场值得庆贺的胜利,却也是一位文人在时代下的落寞悲剧。
学贯中西,狂儒怪杰
虽然辜鸿铭留给大家最深的印象是长袍马褂和清朝辫子,但他从小的生长环境却是在国外,是一个混血儿。
十岁以前,辜鸿铭生活在南洋一座巨大的橡胶园内,他的父亲是跟随祖辈迁居到此的中国人,受雇于橡胶园园主成为该园的主管,他的母亲则是一位生活在此的西洋人。
因为这样特殊的家庭组成,辜鸿铭一出生就有一个非常好的语言环境,日常生活中每天都会听到英语、葡萄牙语和马来西亚语。
而且,橡胶园的园主刚好没有子女,看到小小年纪就聪明伶俐的辜鸿铭便十分喜欢,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来疼,家里的许多名著藏书都完全向他开放,由他任意阅读。
当时是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晚清都还没有进行维新运动,西学中用的风潮也还没有席卷社会,而辜鸿铭已经在幼年时代学习莎士比亚、培根等外国大家的作品了。
后来橡胶园园主要离开南洋回到西方的日不落帝国,出于对辜鸿铭的喜爱,他向辜鸿铭的父亲提出要把他一起带上,让他见识更大的世面,学习更多有用的东西。
辜的父亲对他的孩子寄予厚望,他同意了这个要求,只是作为一位身处异乡的中华儿女,送别儿子之前,他有一句话必须要讲给年仅十岁的辜鸿铭听。
辜父告诉辜鸿铭,一定要记住他是一个中国人,即使未来会身处不同的国家环境,结交不同国家的人,但他中国人的这个身份始终都不会改变。
虽然辜鸿铭那时的年纪还小,可父亲在祖宗牌位前对他说这句话的情景却一直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
此后他在德国和英国的几所著名大学学习各种知识,接连攻读了十三个学科博士,掌握了多种语言,在国外名声大噪受到众人追捧,但他也没有忘记,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有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是他还未蒙面的故乡,而他是一个中国人。
二十四岁的时候,辜鸿铭结束了自己在西方的求学生活,又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南洋。
然后他遇见了一位促使他走向中华文化道路的良友马建忠,马建忠也是一位兼学中西文化的新式人才,在他们两人畅聊的过程中。
辜鸿铭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突然意识到,他学习了那么多的外国知识和语言,用各种被赞誉为精妙绝伦的语言作诗写文章,却还没有去了解一个已经发展了三千年的文化。
于是辜鸿铭又将自己的所有精力埋入国学之中诚信配资,走上了研究中国文化的道路。
与以往的学习不同的是,辜鸿铭第一次体会到学无止境的感觉,中国文化在他心里既如高山又如大海,需要他不断攀登不断前进地去学习。
在这个过程中,辜鸿铭对中西方文化的态度有了非常明显的区别,他认为西方文化不如东方文化,并且还公开在报纸上嘲讽西方文化,同时他也毅然决然地扛起了宣传中国文化的旗帜。
辜鸿铭的表现在当时的外人眼中十分狂妄又十分怪异,因为中国在那个时期正在面临西方国家的侵略,落后的标签已经被贴在了国家的骨血里,国内的有识之士都在纷纷建议向西方学习他们的先进文化,翻译外国著作,辜鸿铭却昂首走向人群的逆流方向。
文化之争,不可收场
1885年的时候,辜鸿铭的双脚终于踏在了故国的土地上。
他受任于晚清政府协助其开展洋务运动,但自己仍旧在钻研国学经典,向世界宣扬东方文化的价值,他的长辫子和长袍马褂已经彻底取代了过去在国外的西装形象,并且难以再除去。
辛亥革命以后,晚清政府彻底倒台,辜鸿铭便也无官可做了,于1914年进入北京大学成为了一名老师,为学生们讲解英国文学,这期间他出版和翻译的国学著作每次都能在国外引起巨大的轰动。
与之相反的是,国内的新文化思潮掀起了一股极强的风暴,将中华文化吹得有些摇摇欲坠。
为了解放腐朽落后的社会,新文化运动在社会上宣扬新的思想与文化,反对陈旧的东西,他们还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打倒孔教儒学。
这些口号言论戳到了辜鸿铭等旧文化卫道者的逆鳞,气得他们纷纷表明要抵制新文化,新旧文化之间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
而蔡元培当上了北大校长以后,便把这个“激烈的战场”搬进了校园内,使民国时期的北大焕发出耀眼的生机。
但其实新旧文化之争本身存在着一些误会。
比如新文化的领头羊陈独秀对中华文化的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对孔子儒学的反对主要是政治上的,而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则是为了提高普通人的受教育程度,他本人在北京大学任职期间还编纂过国学书籍。
只是新文化运动中也不乏激进人士,这其中表现特别突出的便是钱玄同,他竟然提出了直接废除汉字。
这便是辜鸿铭最担心的一点,他害怕国学经典在这一场运动中彻底被中国抛弃,那将会造成国家的巨大损失,作为国学正统的维护者,尤其是儒学的推崇者,他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双方的冲突愈发激烈,他们以各自支持的文化作为武器,以报纸期刊作为演武场,彼此之间你来我往,互不相让。
落寞收场,文明脊梁
而辜鸿铭在与新文化的交锋中,和胡适之间更是结下了无法解开的梁子。
作为一个在国内外声名鹊起的学者,辜鸿铭自有一股傲气,年纪轻轻留洋归来的胡适在他面前不过是一个黄毛小儿。
更何况胡适当时被聘为北大教授的时候还没有取得博士学位,在辜鸿铭的眼里,他就是凭借新文化运动的“明星效应”才获得和大师级的人物一起共事的机会。
从胡适被请进北大的那一天开始,辜鸿铭便集中火力对准专门向他开炮,基本上胡适做什么他都要跟着嘲讽或者反对,而他们两个在思想观念上的完全相反则加大了彼此之间的矛盾。
曾经胡适在课堂上提出应该用西方的理论来评估中国文化的价值,被辜鸿铭知道以后转头就对自己的学生说,他教授学生英文知识,是培养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不是在培养西方的奴隶,直接表达了对胡适的嗤之以鼻。
而胡适也同样不甘示弱,写文章批评辜鸿铭的“长辫子”。
文化人在口头上的斗嘴吵架在蔡元培的眼里不算什么大事,除了适时的调和一下,他非常乐意看到类似百家争鸣的思想火花在北大的校园绽放,因此他虽然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却也非常礼遇辜鸿铭这样的国学大才。
所以辜鸿铭从未把枪头指向蔡元培,还处处维护他,他心里也明白,学校的新文化风潮正是最热烈的时候,学生们大都追求新思想,如果不是蔡元培,恐怕自己早就保不住饭碗了。
可是出了文化之争的范围外,蔡元培便也无法出面保下辜鸿铭了。
辜鸿铭除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卫道者以外,受儒家思想的“天地君亲师”影响,他还是彻彻底底的保皇派,虽然他不保慈禧、袁世凯这样的昏庸之人,但他却还是封建帝制的拥护者,这才是他与时代潮流真正背道而驰的地方。
文化相争的背后还有政治相争,而辜鸿铭便是因为自己的政治立场才彻底输掉的。
根据学生们反映,辜鸿铭每次上课不到几分钟就开始讲所谓的“君师主义”,向学生们鼓吹封建帝制,这让思想先进的学生十分不满,便将他告到了校长那里。
而带头的那个人便是胡适的学生。
这件事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这跟以往的文化斗争已经不再一样了,学生们的愤怒达到了顶峰,封建帝制的压迫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这确实是被辜鸿铭忽略了,或者应该说他从未体会过。
当局政府知道这件事以后也对辜鸿铭非常不满。为了平息众怒,让校园重回平静,胡适便私下向蔡元培提议解聘辜鸿铭,但对外的说辞是他自行选择离开的。
蔡元培别无他法,这已经是最好的处理方式了,于是辜鸿铭就这样离开了北京大学。
钱玄同等人听闻这个消息自然是非常开心,校园中又少了一个守旧顽固派,新文化运动的阻力也少了一分。
而离开北大的辜鸿铭还在坚定地保皇,孜孜不倦地传扬中国文化,他到日本和台湾讲学,还在北京接待过访华的泰戈尔,除此之外,他找不到自己该待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了。
最后,他死在了即将上任山东大学校长的那一年。
后来人看辜鸿铭总要感叹他是生错了时代,如果辜鸿铭生在当今社会,必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也是毫无争议的爱国者。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如果,虽然辜鸿铭在国家极度自卑的时刻,以绝对的文化自信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耀眼璀璨,在新文化运动少数的极端偏颇之中,以坚定的决心维护传统文化的地位,可是他终究站在了时代发展的末端。
所以辜鸿铭最后的结局便也只能被时代抛弃,实在是让人为他感到可悲可叹。
不过庆幸的是,后人看到了他为国家文化的宣传所做的贡献,他的辫子不再是人们唯一的关注点诚信配资,人们还能看到他昂首挺胸的脊梁。
发布于:天津市科元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